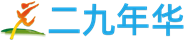范曾:做“五爱”之人
做“五爱”之人
——在南开艺术校友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
范曾
在南开的回忆充满了理想、奋斗、欢乐,种种的回忆,都使我感到这是人生最宝贵的收获。我想南开和我是一个永远割舍不开的最美妙的际遇。在这里有我尊重的教授,虽然他们大部分都已经离世了。我有很多老朋友,像宁宗一先生,我当时聘请他做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的时候,他还是风华正茂的时节,今天已经和我一样白发苍苍了。“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是必然的规律。可是我知道,今天来到会场的,无论是我的朋友、同事、学生,都会知道我在南开所做的事情,是很有意味的。意味在什么地方呢?我今天提出一个“五爱”,我们要爱党、爱国、爱南开、爱人生、爱艺术。
为什么爱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华诞,证明了一点,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不可能从一个苦难深重的泥淖里,走到今天这样的辉煌。虽然我们的祖国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可是她生长着,强大着,富裕起来,这是我们一个根本的事实。
南开大学的存在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这一百年,由筚路蓝缕起家,而到今天如此辉煌。最令人兴奋的就是今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们南开大学,他不仅详细地观看了我们的校史展,而且与我们南开的专家、学生进行了交流,他说南开是一所爱国的学校,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习近平总书记对南开大学的办学精神、校训、“爱国三问”,都做了非常透彻的解释。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总书记对我们南开大学发自内心的关怀。他的讲话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他对我们南开大学寄托了很深厚的期望,这一点我非常感动。这是南开历史上的大事。
今天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大概是几十年前遗留下来的观念,讲北大可以用一个“官”字代表,清华是“洋”,南开是“土”。这种解释我想有一个历史源流,但是并不全面,其实“官”“洋”“土”并不足以完整描述一所大学。“官”,就是说北京大学建立时,首任总教习吴汝纶,当然是大官僚,他本身是曾国藩的手下,又做过冀州知州,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而且吴汝纶也是大学问家。清华大学是由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大学。我们南开大学要论接地气的话,地气接得更多。张伯苓和严修到处筹集资金,到处奔走。在抗战时期,我们这里被夷为平地。在这样悲惨的时候,张伯苓先生是怎样坚持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西南联大是怎样体现中国民族的知识分子临危不惧、坚持奋斗精神的?北大、清华、南开曾经共同谱写过壮丽之歌,不管他们是“官”“洋”,还是“土”。这个“土”,我想说南开大学从来根植于民族精神。就拿东方艺术系来讲,我从来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党的十九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文化自信。在《人民论坛》上,我先后发表过8篇文章,论中国的文化自信、中国的哲学自信、中国的历史自信、中国的文学自信、中国的诗的自信,还有艺术、书法等。
我想,我们作为南开人,时时刻刻都要想到自己和南开大学的关系。因为我们以什么爱国?我想以我们的艺术爱国。我们要以中华民族自己的面貌走向世界,告诉人类有这样一个族群,他们的艺术是如此高雅。我在国外获得的勋章,从来不愿在国内宣扬,像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亲自授予我的“大将军勋章”,它是以意大利共和国号令的形式发布的,而且下面有意大利总统和总理两个人的签名。法国总统也授予我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当时法国总统萨科齐给我的一封信,说“法兰西向你致敬!”我说的这些在座的各位都没听说过,因为我在国内不喜欢宣传这个。我觉得党给我的光荣最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单独表扬了我,我以为自豪。
我们要爱人生。生命对我们来讲非常短促。宇宙是多么悠久,以几百亿年来计算,地球有四十多亿年的历史。我们“生年不满百”,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满百。我觉得满百还不够,希望能有一百多岁,我希望自己能以自己的残年余力与新一代的艺术家共同奋斗,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我81岁了,今天上午坐在从北京到天津的汽车上,把《北山移文》从头到尾背写了下来。这种习惯使我对电脑心存怀疑。很多熟悉电脑的人,谈起话来一说起引文不知道在何处,一查就查的很准,可是这个东西不是你的。我不太会用手机,只会往外打,打完就关,连信号都不给它。因为我对机械的东西有本能的抵制,这很不符合时代的精神,可是很难要求每一个艺术家都符合时代精神,我不去搞大数据,我的画未必不能这么好,因为我不懂电脑我照样画得好。就像陈省身先生根本不会电脑,而且算术水平相当低下。因为有次他在凯悦饭店请我吃饭,他要请客,几十块算了半天也算不下来,我才知道数学和算术是两回事。有次我到清华大学,清华不是“洋”吗,他们请我讲演,我要杀一杀同学们的威风,我说问你们一个问题,1/2+2/3+3/4+4/5等于多少,这些理科的高材生面面相觑,我告诉他们,等于2 43/60,因为2、3、4、5最小公倍数就是60。我说不要被我吓倒,这是汉代《九章算术》里的一个题目而已,大家哄堂大笑,就愉快了。愉快了就随便听我讲,都相信了。在北大文学院开学典礼上,我说有些书你们作为文学院的学生,一定要经常放在手边,唐宋时代的文人,在床边都有4本书,史汉庄骚——《史记》《汉书》《庄子》《楚辞》,这4部书文人是必须熟读的。到明末清初,金圣叹提出六才子书,《汉书》不要了,因为《汉书》和《史记》体例一样。《史记》《庄子》《楚辞》《杜诗》《水浒传》《西厢记》,我就问大家,怎么没有《红楼梦》啊?一个也没有回答上来,我说曹雪芹还没生下来呢。所以针对不同的学生,他们固然在技艺上各有所长,忽然提一个他不了解的事情,这个是最有趣的,当然这里面我个人也想开开玩笑。当年我请宁宗一和薛宝琨这两位名教授到东方艺术系执教,他们在中文系才高气足,很多教授又对他们不服气,结果他们课讲得好极了。宁宗一先生讲唐宋诗词,大家现在都记得。当时薛宝琨先生讲,我们两个有“弃妇”的感情。我说不会,东方艺术系不是真正有才华的人去不了,不会被抛弃,我想诸位要使自己在社会上,在世界上,在多方面立定脚跟,有一个根本的标准,就是自己强大不强大。自己不强大,埋怨是没有用的。
我希望诸位不要太相信电脑。庄子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有了机心,人类就要堕落了。如果现在的科学技术发展下去,它的危险性非常大。前些天北大的前校长周其凤、王恩哥和我谈起科技的发展,到底害处和益处在哪儿。有个生物学家,他说克隆人很容易,克隆人和克隆猴子没区别。我们现在可以克隆出一个人来,可是道德伦理不允许。我说,如果做这个事,危险性就大了。有身强力壮、头脑简单、爱劳动的,拿他的基因塑造一个人,克隆十万个劳动大军,任劳任怨,不讲报酬,新的奴隶社会就出现了。那个生物学家就说,你的思想很新潮啊,现在外面的科学家也和你发表同样的论点。我说我可没看他们的,我自己想的。所以我们还是安分守己一点,拿起自己的笔画画,这是任何科学承担不了的。清华大学的姚期智先生跟我讲,现在的电脑能够制作出一首歌,是之前绝对没有被创作出来的,原创的歌。我问姚期智先生:能不能克隆出来一个范曾啊?他说,这个绝对不能,因为你画画的每一笔都是心智的流泻,而心智瞬息万变。当然未来的科学我不知道。潘建伟先生到我家来,他讲量子每秒以几千亿亿次的速度振动。我说你们怎么知道的。他说我们是计算出来的。我说,就算以再快的速度,把《康熙字典》48000字排列组合,选出生字,能写出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两句诗,我就服了。潘建伟先生说这个是很难的。所以科技不是万能的,人类要永远走在工具理性的前面。而走在工具理性前面的排头兵,应该是文学家、艺术家。诸位,再见。
(南开大学新闻中心林栋整理)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大学门户 » 范曾:做“五爱”之人
相关推荐
- 南开研究生角逐十佳“微党课”140名新任党支部书记研修结业
- 校领导会见帕沃黑尔院士
- 【迎百年校庆】招衡教授做客“百年南开大讲坛”
- 《中国社会科学》刊发我校师生论文
- 2022年第54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公开征集宣传语
-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第十八届年会在南开举行
- 南开大学细胞应答交叉科学中心揭牌
- 陈宗胜 胡熙:把深圳打造成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李兴旺一行来访
- 《刘泽华全集》发布会暨刘泽华学术思想研讨会举行
- 南开大学2021年重要新闻回顾
- 【迎百年校庆】曹雪涛会见南开南通校友会代表
- 2020年数学“双一流”建设联盟会议在津举行
- 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获“天津市先进社会组织”荣誉称号
-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研讨会南开举行
- 南开大学助力定点扶贫县运用生物技术种出绿色蔬菜
- 我心中的数学完人──忆陈省身先生
-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20年年会在津召开
- 宁宗一:一部南开人的心灵史
- 育人成果绽放表演舞台
新闻公告
- 学校召开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03-16
- “南开大学—金泽大学交流日”线上举行 03-16
- 天津市领导来校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03-16
- 南开教授为“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作主题讲座 03-15
- 我校参加全国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 03-15
- 天津市教育两委相关领导来校督导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03-15
- 南开大学牵头成立“大思政课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03-14
高考招生
- 南开大学2018年招生章程 08-05
- 南开大学2017年本科生招生章程 08-05
- 南开大学2016年本科生招生章程 08-05
- 南开大学2013年本科生招生章程 08-05
- 南开大学2014年本科生招生章程 08-05
- 南开大学2015年本科生招生章程 08-05
- 南開大學2013年招收香港地區免試生章程 08-05
- 南开大学2009年本科生招生章程 08-05
- 南开大学2011年本科生招生章程 08-05
- 南开大学2012年本科生招生章程 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