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婴儿:一场代价巨大教训惨痛的全民科普

自11月26日中午,媒体曝出《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后,短短3天,基因编辑技术、辅助生殖技术、“基因手术刀”CRISPR/Cas9、CCR5基因敲除、艾滋病阻断疗法、人类胚胎研究“14天”法则、科学伦理风险……这些原本晦涩难懂的科学术语、专业知识,竟因这样一件“细思极恐”的事件引起了人们热议。
这无疑是一场“成功”的全民科普,它轻而易举地吸引了国人乃至全世界的关注目光,然而,却以牺牲中国科研人员、科研活动、科学教育的信誉和形象为代价,其教训可谓惨痛。
作为科研创新的重镇,未来科学家的摇篮,高校应主动肩负起培养科研人才、传播科学知识、崇尚科学精神、恪守科研道德、敬畏伦理规范的重任。带着关于“基因编辑婴儿”的种种疑问,南开大学师生关注的目光第一时间集中于生命科学学院,期待南开专家给予专业的解读。
经过紧张的筹备,27日晚,第五期“生命之美”热点讲座在生物站报告厅举办,生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陈凌懿教授担纲主讲,探讨的话题正是《基因编辑婴儿与科学伦理》。
当天,讲座现场挤满了听众,有人站在过道甚至席地而坐。除了生科院本院师生外,讲座还吸引了许多文科学院师生、学校管理干部以及公共媒体的记者。面对青年学生,陈凌懿反复强调,科学研究必须尊重生命,科学伦理的高压线不容触碰。
魔盒还是神灯?已有明确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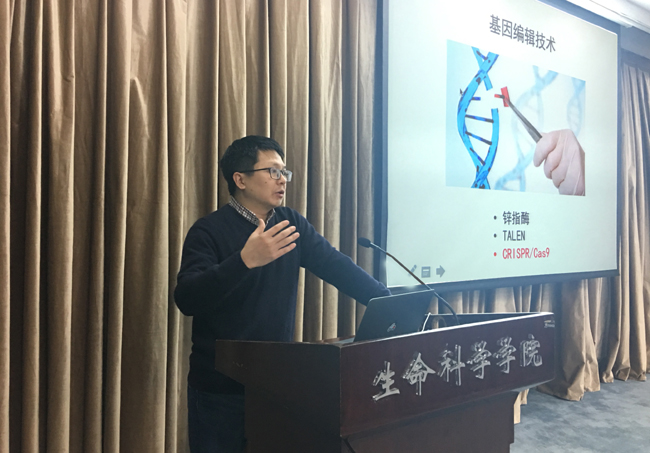
“基因编辑婴儿”的消息报道之初,似乎带着一种“重大突破”的自豪感。对于广大普通人来说,也容易被其宣称的抗艾疗效所迷惑。短时间内,甚至有“潘多拉的魔盒”与“阿拉丁的神灯”之争。然而,随着更多科学界声音的发出,这一“重大突破”的色彩发生了改变。人们很快发现,所谓的“重大突破”并不代表技术的进步,它所突破的是人类科学家一直以来努力持守的科学伦理底线。
陈凌懿介绍,“基因编辑婴儿”是辅助生殖技术与基因编辑技术相结合而诞生的,其中包含着巨大的科学伦理风险。
科技部与原卫生部在2003年颁布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中明确规定了人类胚胎研究的“14天法则”:“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人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不得将前款中获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原卫生部制定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也明确规定,“禁止以生殖为目的对人类配子、合子和胚胎进行基因操作”。
“基因编辑婴儿”项目,严重违反了上述规定。11月29日,国家卫健委、科技部、中国科协负责人分别回应“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已要求有关单位暂停相关人员的科研活动、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
“基因编辑婴儿”项目也受到了科学界的强烈反对。
事件发生后,百余位中国科学家发表联署声明,对于在现阶段不经严格伦理和安全性审查,贸然进行人体胚胎基因编辑的任何尝试,表示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的两位共同发明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与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系教授詹妮弗·杜德娜和华人生物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张锋,分别发表声明表示反对。
140名海内外华裔艾滋病研究专业人士27日午间发表公开信称,“坚决反对这种无视科学和伦理道德底线的行为,反对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未得到证实的基础上,开展针对人类健康受精卵和胚胎基因修饰和编辑研究”。
“我们强烈谴责在现阶段把基因编辑用于人体实验,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尚不成熟和伦理严格限制。”在陈凌懿看来,中国科学家、专业学会联合发声,正是我国学术界对科学伦理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珍视的体现。
陈凌懿教授同时表示,基因编辑技术除了可能对新生儿健康成长带来潜在风险外,也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想变漂亮的人,变聪明的人,都能改变自己或者后代的基因,可能会产生很多负面的社会问题。如果用在军事上,那后果将不可想象。”陈凌懿说。
基因编辑婴儿免疫HIV?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贺建奎声称,CCR5基因敲除后的双胞胎姐妹,出生后能天然抵抗艾滋病。对此,陈凌懿表示,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CCR5不只是HIV的‘内奸’。研究表明,它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作用。”陈凌懿说,小鼠实验证明CCR5对心血管、造血系统、免疫系统发育具有重要作用,敲除后可能产生上述部位发育缺陷,甚至导致一些病毒感染更严重,如West Nile(西尼罗)病毒。
同时,艾滋病病毒有众多变种,在我国主要的流行亚型是CRF_BC、B’和CRF_AE,而CRF_AE亚型HIV侵染T细胞不依赖于CCR5基因。“也就是说,敲除CCR5基因的婴儿只能防御部分艾滋病病毒变种,而无法实现天然抵抗艾滋病的目标。”陈凌懿说。
此外,基因编辑本身就存在一定的技术风险,比如脱靶效应。即,编辑了目标基因片段的同时,对别的基因片段产生影响。或者,根本没有作用到目标片段。“这些都是潜在的风险,以目前的技术水平,我们很难保证其安全性。”
医学领域尝试新的治疗方法,前提一定是没有更好的方法可用。然而,对抗艾滋真的只有基因编辑这一条路可走吗?实则不然。在艾滋病病毒防治中,临床上早已有了成熟的办法,一些药物或疗法可以很有效阻断HIV病毒由父母传给后代,且成功率非常理想。
“我们何苦做这样尝试,还要让婴儿面临脱靶风险,显然收益和风险完全不对等。”陈凌懿说,因编辑婴儿试验必须要告知病人本人存在的风险并征求其同意,而在这个操作中,病人是胎儿,“在得不到本人同意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利把他改变,让他出生。”
两个婴儿未来将受到怎样的影响,目前是未知的。他们的父母将承担所有的抚养责任,一旦父母的能力无力支撑时,就会加重社会的负担,显然这样的实验得不偿失。
“我们身边存在着科学伦理问题。”面对青年学生陈凌懿严正地指出,“我们正在进行的动物实验,采集的病例样本、个人信息,实验对环境的影响等等都涉及科学伦理。我们不能随意做实验,要按流程提交实验申请,准确估算,以实现最小的动物用量和最大程度地环境保护。”
踊跃提问 激烈讨论

当晚的讲座,陈凌懿主讲的内容只有40分钟,而提问环节持续了一个小时,直到活动结束,仍有几个同学围着陈凌懿讨论。
一位人权中心的青年教师谈到,虽然目前学界对此次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进行集体谴责,但对于此类事件出现的惩戒仍缺乏相关法律依据,只能依靠行业自律。“技术成熟的速度一日千里,法律规范显然落后,二者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法律一般都会滞后于事件,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科学家、法学家、人文学者共同解决。”陈凌懿说。
一名学生提问,生命科学探索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有尽头吗?人类是否应该保留生命科学探索的一片禁地不去触碰?陈凌懿表示,生命科学探索的目标是探索生命的秘密。科学探索是永无尽头的,但科学成果的应用应该是有界的。“科技的进步是无止境的,但是一旦涉及应用层面,我们必须谨慎。现在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人类,并不是一个好的时机。”
有同学提问,“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是不是意味着已经可以或者将要达到令人们感到恐慌的“定制婴儿”的水平?
陈凌懿表示,目前生命科学界对人类基因奥秘的探索才刚刚开始,基因技术存在很大局限。可以说,目前离“定制婴儿”还差的相当遥远,大众不必过于恐慌。“人类能够修饰的基因是有限的,曾有报道介绍,在小鼠体内能同时修饰三、四个基因,这对于整个基因组的优化是明显不够的。何况目前,如何修饰基因,哪些基因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我们还不知道。至少在现阶段,没有必要恐慌。”
现场也有人尖锐地提问,“基因编辑婴儿”项目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其背后是否受资本利益的驱使?当科学与金钱捆绑在一起时,如何有效防止有违科学伦理的事件发生?
“背后是否有利益驱使只能是猜测。但无论如何,要想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一方面需要我们全体科学工作者加强自律,心存敬畏,恪守伦理道德底线;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制度,要让违背规范的行为付出代价。”陈凌懿说。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大学门户 » 基因编辑婴儿:一场代价巨大教训惨痛的全民科普
相关推荐
- “资深翻译家”王宏印:文海漫游 播种真知
- 管健:面对疫情在危机中寻求成长
-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发展:问题和趋势”研讨会云端举行
-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高端学术研讨会举行
- 后台书店有奇缘
- 天津市人才办来我校就人才工作进行上门服务
- 南开师生荣获2021年宝钢优秀教师奖和优秀学生奖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驱动的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研究”开题暨研讨会举行
- 中国科协调宣部部长郭哲一行调研数字经济研究中心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国家重大突发事件信息公开质量研究”开题
- 南开团队在肿瘤靶向型近红外光敏剂研究领域取得新进展
- 天津市科协客人来校访问
- 扬州校友会反哺母校 颁发奖助学金资助南开学子
- “对标争先”学生样板党支部培育创建南开论坛召开
- 南开大学在安徽举行优质生源基地授牌仪式
- 2020南开旅游新年论坛暨南开MTA校友会成立仪式举行
- 中国教育报:“公能”薪火 百年传承 ——写在南开大学百年校庆之际
- 王达津爱逛钱摊
- 我校参加教育部直属系统离退休工作通气会
- 南开大学终身教授王伟光在《求是》杂志发表理论文章
新闻公告
- 学校召开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03-16
- “南开大学—金泽大学交流日”线上举行 03-16
- 天津市领导来校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03-16
- 南开教授为“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作主题讲座 03-15
- 我校参加全国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 03-15
- 天津市教育两委相关领导来校督导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03-15
- 南开大学牵头成立“大思政课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03-14
高考招生
- 南开大学2018年招生章程 08-05
- 南开大学2017年本科生招生章程 08-05
- 南开大学2016年本科生招生章程 08-05
- 南开大学2013年本科生招生章程 08-05
- 南开大学2014年本科生招生章程 08-05
- 南开大学2015年本科生招生章程 08-05
- 南開大學2013年招收香港地區免試生章程 08-05
- 南开大学2009年本科生招生章程 08-05
- 南开大学2011年本科生招生章程 08-05
- 南开大学2012年本科生招生章程 08-05
